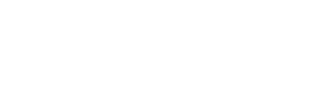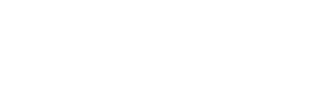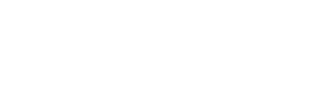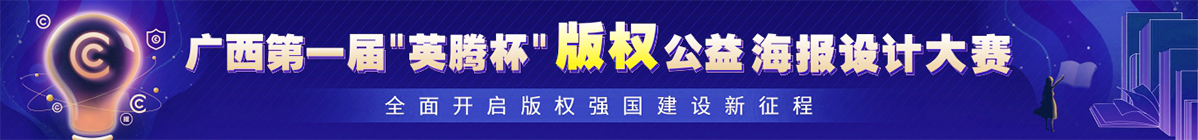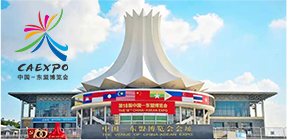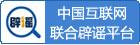原标题:广西文坛老将常弼宇笔耕不辍,倾情倾力于第一部长篇小说
“壮乡山歌滋润了我的心田”
常弼宇祖籍北京,出生在广西平果,10个月大后离开平果,之后在德保县生活了24年,现在的他已在南宁生活多年。这位广西文坛的老将,至今笔耕不辍。在老壶馆里他述说着自己的文学之路。

常弼宇认为用北方文化的视角欣赏南方文化,会有新收获。
在传统中寻变 平静的文坛里掀起涟漪
“当时正处于特殊期间,学校停课。我就常常和同学两个人跑到德保县中学图书馆看书。”谈起与书的结缘,常弼宇说他从小就爱看书,这好习惯主要得益于读小学时那位和他一块去图书馆看书的同学,“我一个同学的父亲是管图书馆的。拿了钥匙后,我们就钻进去看书,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,什么书都翻来看。”初次接触书时,常弼宇就有了“挑书来读”的条件。“当时一个小县城中学的图书馆,其实藏书量并不多,但是对于一个小学生来说,却是足够的。”常弼宇回想自己少年时期看书的这段经历时,眼里放着光,“也许有些书不是实用的,但它的确能够予你启迪。”
在常弼宇的创作道路上,正是这样一本本书,让他得到不断的积累,激励他前行,让他明白一名作家起码的要求,就是认真读一定量有益的书,从而引发更多的思考。
提起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广西作家和评论家,不得不提的是“百越境界”和“广西文坛88新反思”。有人说,正是先有这些作家和评论家,才有后面的“文学桂军”。而常弼宇正是“广西文坛88新反思”的成员之一。
1988年秋天,时任广西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编辑的喜宏说,当时广西文坛太平静了,没几个作家能够走向全国,文学界应该好好讨论一下。于是乎,在与几位作家朋友讨论之后,当时已经从德保来到南宁工作,在《影剧艺术》担任编辑的常弼宇便和好友杨长勋、黄神彪、韦家武以及黄佩华五人针对广西文坛的现状,提出了“在传统风格中寻变”“提倡包容文学风格的多样性”等主张,并各自撰写一篇评论文章,最终形成了一个评论文章系列合集。
1889年初,这个主题为“广西文坛88新反思”的合集在《广西文学》刊发,引起了广西文学界的讨论。提及“广西文坛88新反思”,作家黄佩华回忆道,“一时间,广西文坛似是静潭里投下了巨石,掀起了一阵不大不小的涟漪”。
关注边缘人物 平凡人物也不乏闪光点
常弼宇对自己小说的评价归结于“思考”。“小说创作开端起步其实跟有感而发有关。”他说,当时小说看得多了,总结发现作品中缺少社会底层活生生的人物,于是他试着将这些缺席的人物补进去。
事实上,从常弼宇的第一篇小说《山圩二人传》开始,他就为自己创作的小说定下了“思考”的基调,也是开始了他对小人物的关注。他认为,由于历史的原因,边缘化的人物和他们的生活成为野史,其实他们应该是正史中的人物,也应该是文学关注的人物。
《山圩二人传》中有一位头部负伤转业回乡在水管所的黄叔。尽管这位黄叔平日里表现得很迷糊,但身上却时刻散发出淳朴、善良的光芒。小说中有一个片段令人印象深刻:当时坐马车出行赶圩时,和黄叔熟悉的人会偶尔拿他开玩笑,起哄赶他下车,但黄叔却并不在意,心想下车等下一辆马车就是了。而生活中的黄叔心底很善良,会救济那些缺吃少穿的人,在雨天还会将大家迎进家里避雨。
“我的小说的主角原型大多是德保县的一些边缘人物。”常弼宇坦言,之所以喜欢写边缘人物形象,是因为从这些人物的身上,他能够看到某种坚守。而他认为,即便是在边缘人物身上,也不乏充满人性光芒的闪光点。常弼宇认为,从作者的角度来看,边缘人物的故事相对应的其实是励志故事。“我们现在很多作家或者有志于文学的初学者会非常喜欢听励志故事,但现实中每一个人的人生道路都是不可复制的。”常弼宇说,他更想讲那些鲜有励志故事的普通人和事。
不断推翻重写 倾力于第一部长篇小说
常弼宇毕业于广西大学中文系。200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。他曾担任广西作协副主席。他著有小说集《误入野史》《籍贯》等,另有中短篇小说发表在《当代》《青年文学》《上海文学》等刊物上。而他自认为还缺一点什么。于是,他正努力写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。
这部小说花费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,“一开始写这部小说时,写了几万字,废掉,推倒后又写几万字,又废掉,现在终于可以写下去了。”常弼宇称,这部小说之所以被不断地推翻重写,并不是因为它缺少故事,而是语言。“包括我在内的许多老作家,在语言上受传统文化影响其实是比较大的。”常弼宇笑称,“你们看现在的年轻人啊,他们中又有多少人会愿意去读那些冗长的小说呢?传统小说的叙述过于缓慢,那种唯恐别人不知道的繁杂叙述,年轻人不愿意读啊。”
常弼宇的感慨不无道理,新媒体时代下,文学语言不可避免地受到网络语言的冲击。一方面,语言简单化,扁平化的趋势在互联网得到放大。另一方面,近年来,网络语言又出现了用文字拼音首字母拼凑出一个个词组的现象。在常弼宇看来,网络语言影响范围大,但无意于去承担历史和文化之重,“那么在两者中间,你要思考有一种语言,它能够恢复到汉语本身的魅力。”常弼宇坦言,正是这样一种对于语言的追求,支撑他不惜用流水年华换一部长篇小说。
道不尽的情愫 眷恋南方少数民族文化
“南方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精神是非常自由的。”回想起上世纪90年代和《老井》的作者郑义去百色村落采风的那段经历时,常弼宇感慨,“当时我、黄佩华和郑义一起去百色采风,一路下来,我切身而又真实地感受到了南方少数民族淳朴自由的精神世界”。谈起这段百色采风经历,常弼宇似乎有讲不完的故事和道不尽的情愫。“每当夜幕降临,人们结束了一天的劳作,唱起了山歌,整个村子一下子就沉浸在了欢乐的海洋之中。当时的我既惊羡于他们的欢愉,也开始了自己的思考,《歌劫》就是这样来的。”
常弼宇所说的《歌劫》于1993年3月发表在大型文学期刊《当代》。这部小说追溯了一群歌者的命运。小说中,在为爱和智慧而生的歌圩上,一代歌者没有像他们祖辈那般安逸潇洒地活到头,而是面临着对山歌和歌圩的重新选择。在常弼宇的笔下,壮乡山歌和歌圩面临着分化的危机。最终,尽管一代歌者并没有把山歌和歌圩带回到他们历史的原位,但穿过悠长而苦难的岁月,一代歌者毕生歌颂的真挚、古朴、自由、奔放、率真、顽强,在尘埃落定后,终于得以显现,并期待着下一代歌者的继承与弘扬。“我从小受到的是北方文化的熏陶。”尽管长在德保,家庭中北方文化的影响给常弼宇留下了独特的印记。“就像是从北方的那种空旷、干燥中突然掉落到稠密、湿润的亚马逊森林。”常弼宇身上北方文化的元素使他对南方文化有着特殊的敏感。他认为用北方文化的视角欣赏南方文化,会有新收获。“可以说,山歌滋润了壮族人民的精神世界,也滋润了我的心田。”常弼宇感慨。
他像时光倒影中一身青衣长衫的读书人
坐在朋友林先生的老壶馆里,常弼宇说起文坛的往事,冷静却不失幽默,如果瘦高的他换上一身长衫,感觉与多年前、时光倒影里一袭青衣的读书人无异。
常弼宇一直在广西文坛耕耘,他跨越地图上的南北,直奔向文学的主题。百度上几乎查不到他的专访,这位学者型的作家心中怀有巨大的理想与隐忍,他就静静地坐在城市一隅,沉默得像王家卫电影里的某帧镜头一般,任由整个世界呼啸而过。
常弼宇心中有三个故乡。祖籍北京,德保以及如今生活的南宁。故乡对于常弼宇而言,更重要的是它的人文属性。人文属性一言以蔽之,就是人的生存劳作表现与气质。北方故乡物理属性的广袤大地,沉默无语,未来可期给他印象难忘。在德保,山歌如同漫山遍野的泉眼日夜涌动。那里的人们曾经以形象生动悦耳的语言认定亲疏,那里的人们不受外界影响,一直守着古老的传统。而南宁是一个焕然一新的城市,是让少小离家老大回的乡亲迷路的城市。因为人口结构的改变,南宁的老风物流失时,痛心的人声音薄弱。一得一失之间,快乐的人还是多数,所以城市保持了祥和。(记者 李宗文 实习生 徐健翔)
(责任编辑:郑友)